五四青年 魯迅的北京歲月

魯迅曾居住過的北京西城區磚塔衚衕84號。(中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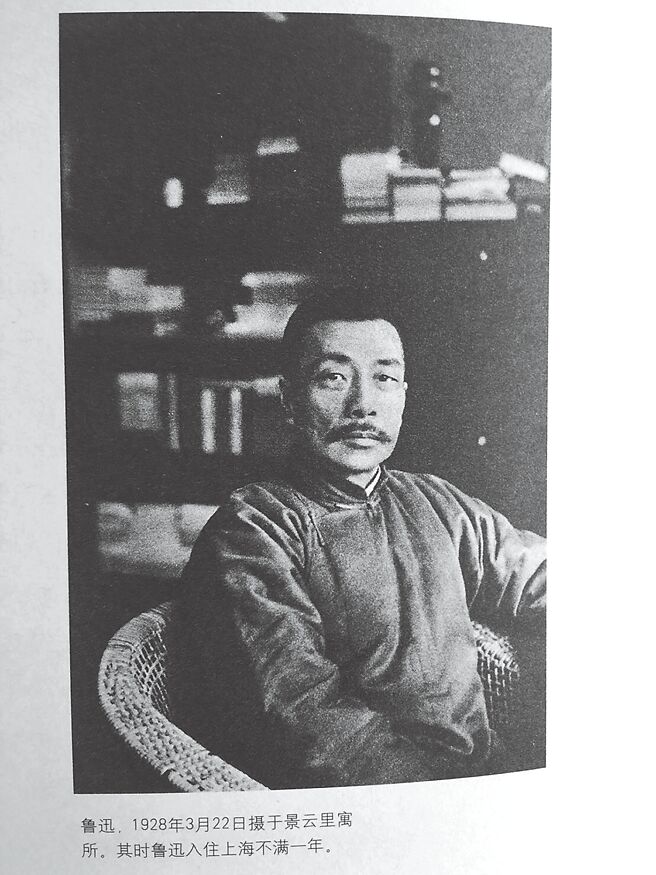
魯迅來自紹興,作品中多有故鄉身影。(本報資料照片)
《城市異鄉人》以北京和上海兩座城市,試圖以此打開五四世代心靈深處「黑暗的閘門」之謎。(聯經文化提供)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魯迅搭船抵達天津,再轉搭火車於七點抵達北京,而這一天對他來說必然是重要的,因爲現存的《魯迅日記》恰恰就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記載,但他在日記中卻是這樣寫的:「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似乎對於眼前這一座歷史悠久的偉大皇城,只有說不出的冷漠與淡然。
北京城與宣南會館區
事實上一九一二年魯迅所行走的一條進京的道路和生活空間,與晚清的文人如康有爲或梁啓超等並沒有太大不同,魯迅所任職的教育部就是原來滿清的學部,位在宣武門內的教育部街,而魯迅所落腳的住處紹興會館,在日記中他仍是沿用舊名「山邑會館」,而在《吶喊》序言中他則把它稱之爲是「S會館」,則是位在宣武門外的南半截衚衕。這一帶號稱是北京城南的會館區,除了紹興會館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大大小小會館,多是從明朝時就陸續興起,乃是以同鄉作爲單位,專門提供給全國各地世子進京趕考時居住的所在。又因爲舉辦鄉試的考場貢院就位在東單牌樓的貢院東西街,所以基於地理上的方便,絕大多數的會館就集中在前門、崇文門以及宣武門以南,一直髮展到清末儼然已經成了北京城市中的人文薈萃之地,文化商業活動發達,也因此誕生了知名的古董文物集散中心:琉璃廠。從《魯迅日記》看來,他入京之後幾乎每天都會到琉璃廠尋訪各種古籍的珍本,可以說是他在北京最常造訪的所在。
因此若以城市空間的角度而言,北京城乃是一個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完美設計,以紫禁城作爲核心,而四周環繞着一圈正方的城牆,以區隔出皇宮貴族專屬的內城,以及平民百姓居住的外城。至於各個鄉邑如大大小小的蜂巢般集結在城南,也宛如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如此一來,城中央的內城所象徵的乃是「國」之威權,至於城南的會館區則象徵的是「家鄉/故鄉」,而「國」與「家/鄉」就在這座北京城中巧妙的連結在一起,如此的設計可以說是完全迥異於歐洲以中產階級爲主的城市格局,也暗示中國鄉土宗親的紐帶之強大。
知名的法國小說家綠蒂,在一九○○年時以法國海軍的身分加入八國聯軍之役遠征到北京之時,也爲這座城市空間的獨特設計讚歎不已,認爲在西方的城市建築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見,更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渲染儀仗的華美,烘托帝王駕臨的威儀」的中心思想。於是在承平時期,朝廷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召喚全國的知識菁英從各自的家鄉出發,萬川歸海似的匯聚到北京城南會館區,必須遵循嚴謹的考試程序逐步往上攀爬,最終纔有可能進入到內城的權力核心。而如此一條晉仕的途徑,也彷彿是將「家」與「國」以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成功結合在一起。然而若是不幸遭逢到亂世,此一結合鬆動脫落,那麼會館區便會搖身一變而爲凝聚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其中蘊藏豐富的革命潛力。
康有爲與「公車上書」
一八九五年康有爲發動的「公車上書」可以說就是最好的例證,當時恰逢三年一次的會試,會館區因此擠滿了進京趕考的文人,包括來自廣東的康有爲和梁啓超在內。當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的消息傳來,當時仍是一介書生的康有爲立刻聯合梁啓超上書,並在會館區獲得了數千名的舉人響應簽署,一行人浩浩蕩蕩步行到都察院上呈光緒皇帝。從康有爲《我史》的記載,仍可窺見當年「公車上書」的盛況:
(世子們)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
據說康有爲後來透過太監得知自己已經名列進士,才退出了行動,而使得這場「公車上書」到最後不了了之,但卻業已拉開了中國羣衆運動的序幕,也是維新派人士躍上政治舞臺的開始,也因此纔有了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的變法維新。只可惜戊戌變法短短維持了百日,就在慈禧的震怒之下宣告破局。清廷的步軍統領崇禮率緹騎包圍南海會館,一時間「車騎塞米市衚衕口,觀者如山」,而「戊戌六君子」的康廣仁和譚嗣同等人也都在會館之中遭到逮捕,最後未經審訊,就被押往菜市口去問斬處死。
因此當一九一二年魯迅入京後,每天早晨他從位在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出發,前往教育部去點個卯時,走在這一條路上,他勢必會先經過北半截衚衕,也勢必知道那兒就是譚嗣同居住過的瀏陽會館,而他再往前走不到一百公尺就會來到了米市衚衕,那兒便是康有爲居住過的南海會館,一八九五年中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也是現代政黨的雛形「強學會」,就是在那兒成立。如果再往右穿過了兩條衚衕,魯迅就會來到了粉房琉璃街,那兒是梁啓超住過的新會會館,也是傳說之中他第一次把居室命名爲「飲冰室」的所在。昔日變法維新的青年,如今安在哉?當魯迅漫步穿梭在會館區的這些衚衕中時,心中豈能不有所感?
其實從一八九五年康有爲「公車上書」到一九一二年魯迅入京,其間相隔也纔不過十七年而已,乍看之下,北京的巷道和格局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但事實上卻不然。自從滿清垮臺民國成立之後,北京的城牆就陸續遭到拆除,而這也使得昔日區分內城/外城、貴/賤、滿/漢的界線也因此隨之打破,而科舉制度廢除,乃至於軍閥割據,國家主權四分五裂,更是在社會的底層引發了一連串的階級流動,再再使得一九一二年的北京城市的空間象徵意義已和清末截然不同。
換言之,魯迅可以說是親眼目睹北京城市從晚清過渡到現代民國的見證者之一,而他也在作品中呈現出敏銳的空間感受,尤其是他所居住的紹興會館,在他的筆下更成了一個朝代更迭、新舊交替之下,一個知識分子夾縫處境及幽暗心靈的隱喻。在科舉廢除繼之皇城崩解後,會館更彷彿是陷落在「國」與「鄉」的夾縫之中,是進退不得的黑暗地帶。(本文摘自《城市異鄉人:城市.現代小說.五四世代》一書,聯經文化出版)





